在人工智能(AI)领域,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尤其是在硅谷这个科技创新的中心。各大科技巨头如谷歌、Meta、苹果以及新兴的xAI等,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夺顶尖AI人才。这种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量的资金涌向少数顶尖人才,形成了“99%的钱流向1%的人”的现象。
Meta的疯狂挖角
Meta公司及其CEO扎克伯格,在AI人才争夺战中表现得尤为激进。他们不仅通过高薪吸引人才,还通过投资或收购公司的方式来获取顶尖人才。例如,Meta斥巨资收购数据标注公司Scale AI的大量股份,并直接任命其年轻的CEO为Meta的首席AI官。此外,Meta还瞄准了OpenAI、谷歌等公司的顶级研究员,开出了高达数亿美元的薪酬包。
为了吸引OpenAI的核心成员,Meta甚至开出了“4年3亿美元”级别的薪酬,第一年就能兑现一大笔股票。尽管Meta声称这种极端报价仅限于少数领导职位,但在科技圈内仍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高薪策略使得OpenAI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甚至被形容为“AI人才超市”。
OpenAI的CEO Sam Altman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试图通过强调公司的使命和文化来留住人才,但也不得不调整薪酬结构,为关键研究人员提供额外的留任奖金和股权。

苹果的无奈与调整
即使是一向高冷的苹果公司,也开始改变其策略以应对AI人才的争夺。苹果过去因为保密文化而不鼓励研究员发表论文,这使得它在吸引AI顶尖学者方面面临挑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苹果开始放松一些限制,并大举投资内部大模型项目。然而,即使如此,苹果负责基础模型研究的主管仍然被Meta以超过1亿美元的薪酬挖走,苹果并未尝试反挖或匹配Meta的报价。
华人面孔的崛起
在这场AI人才争夺战中,华人面孔的出现频率非常高。许多顶尖的AI研究人员都具有华人背景。例如,余嘉辉、彭若明、常慧文等,他们都在AI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余嘉辉,中科大少年班出身,曾在谷歌DeepMind工作,领导过Gemini多模态项目,后加入OpenAI参与GPT-4o等模型的开发,然后被Meta重金挖走。彭若明,曾在谷歌工作多年,后加入苹果负责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基础模型团队,之后被Meta挖走。Meta为了挖他,据称开出了超过2亿美元的总包。
常慧文,清华大学姚班的毕业生,在谷歌担任研究科学家四年多,于2023年加入OpenAI,参与开发了GPT-4o的图像生成系统。任泓宇,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加入OpenAI后,负责后训练团队,专注语言模型训练优化,是GPT-4o mini等模型的开发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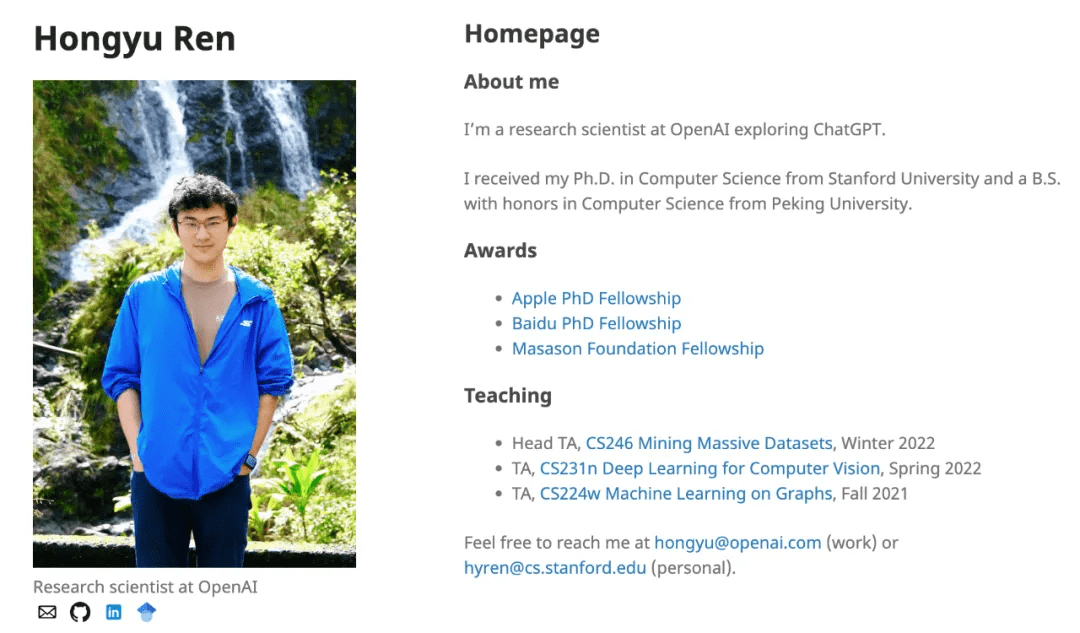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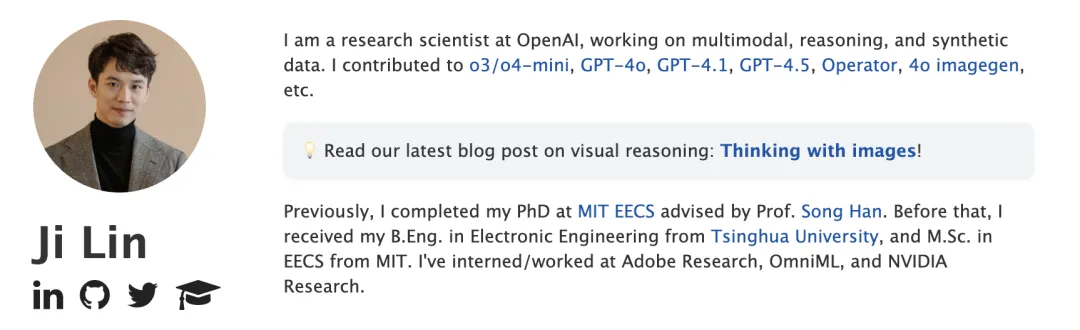
Douglas Chen,Windsurf联合创始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在Meta和Facebook担任机器学习工程师。

苹果公司在彭若明离职后,提拔了另一位华人工程师陈志峰接手,负责Apple Intelligence背后的大语言模型研发与部署。华人面孔在AI领域的崛起并非偶然。据分析,在美国顶尖AI研究人员中,超过三成拥有中国背景,比例甚至略高于美国本土出身的研究人员。
马斯克对华人工程师的倾向也很明显,其团队合照总有很多华人面孔。xAI创立时,12位创始研究员里有5位是华人。在Grok 4的直播发布会上,坐在马斯克旁边频繁露脸的就是吴怀宇(Tony Wu),他是xAI的联合创始人,曾在谷歌DeepMind、OpenAI实习。
“边裁边挖”的背后
然而,在这场天价合同的背后,也隐藏着另一个群体的焦虑。这场挖角大战可能只针对金字塔尖的1%,剩下的99%呢?虽然一些资深的AI工程师也能拿到100万到150万美元的年包,但对于许多硅谷程序员来说,AI的崛起带来的不仅是羡慕,还有切实的危机感。

各大科技巨头在争抢顶尖AI科学家的同时,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Meta、谷歌、亚马逊等公司都在进行人员优化,将资源投向AI项目。微软CEO纳德拉表示,微软内部已有20%至30%的代码由AI生成。随着AICoding效率的提高,普通软件工程师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
一些硅谷软件工程师认为,目前99%的钱流向了1%的顶尖AI人才,AI本身岗位不多,程序员开发的AI取代了很多岗位,最后可能会革了自己的命。
硅谷的AI抢人大战,不只是巨头之间的零和游戏。无论是AI人才、普通软件工程师、还是硅谷巨头,现在都不得不接受这种高流动性和短期主义,以及一个现实:大量的钱、更多的钱,都只流向AI。这场人才争夺战,实际上是AI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资源重新分配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