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AI技术如何深远变革人类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深刻重塑着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关注AI带来的就业替代等具体问题,并积极寻求“怎么办”的解决方案。然而,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在于“怎么看”这场由AI驱动的文明巨变。正如蒸汽机不仅改变了交通方式,更引发了农耕阶级的消亡、工业阶级的崛起以及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AI对社会的影响远超功能层面,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模式与价值准则。
一、超越表象:以“怎么看”理解AI的深刻影响
面对AI的浪潮,许多学者和公众的首要反应是探究其对现有体系的冲击以及应对策略。但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笑宇在其著作《AI文明史》中所强调的,真正关键的问题并非“怎么办”,而是“怎么看”。这一视角转变,促使我们跳出狭隘的功利主义思维,去审视AI技术对人类社会结构、家庭形态、政治体系乃至人际关系模式的全方位重塑。
他提出,理解AI对社会结构冲击的数学基础在于,它在所有需要智能活动的领域,都能以比人类高出数千倍的效率运作。这一效率上的巨大差异,预示着社会结构、教育体系乃至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都将面临根本性的洗牌。这种变革并非遥远,而是将在未来10至20年间逐步显现,其深远程度可能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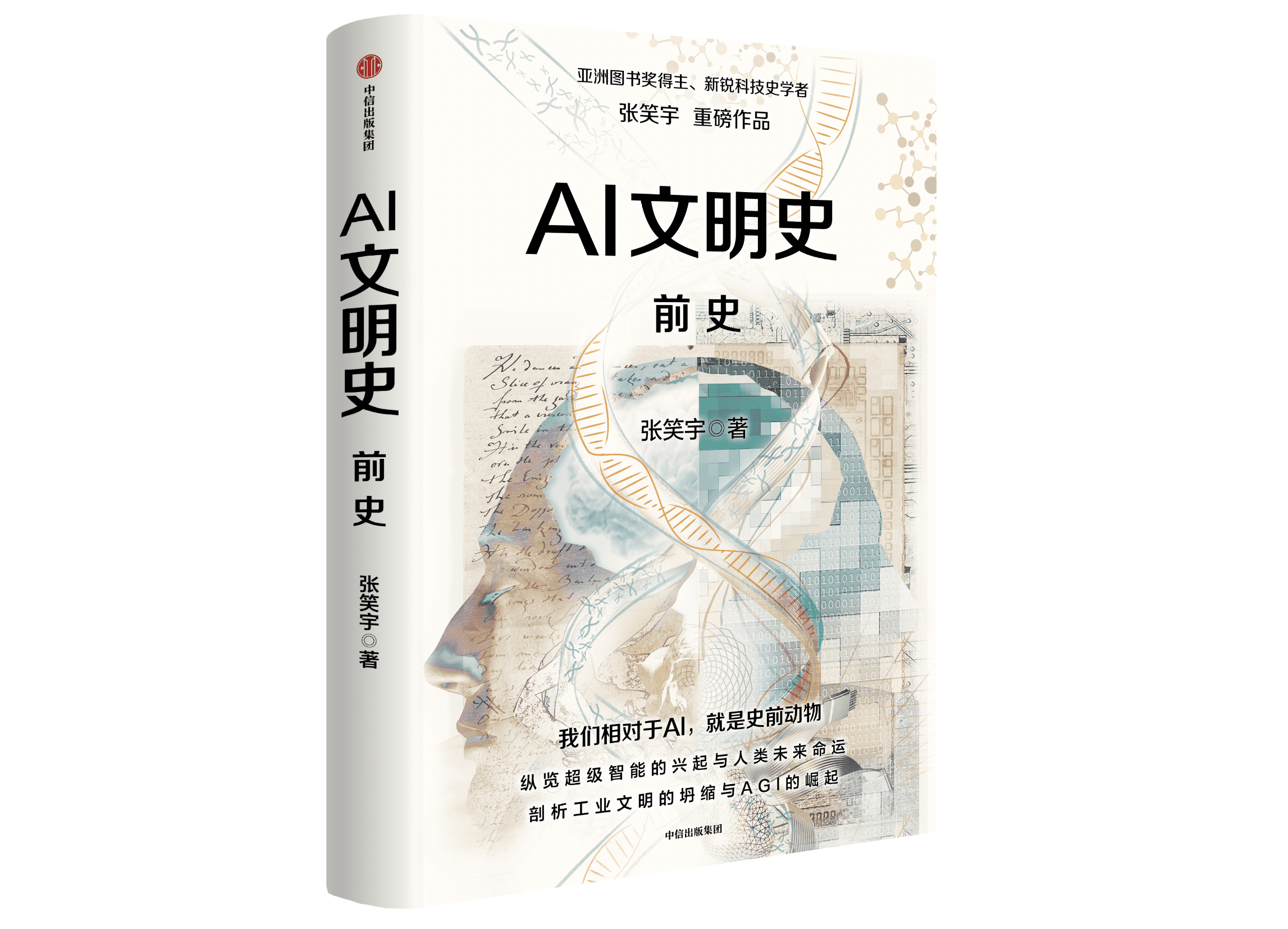
二、AI时代四大基石原理的深度解析
为了更好地“看”清AI的本质及其影响,张笑宇提出了理解AI的四个基本原理:涌现、人类当量、算法审判和文明契约。这些原理构成了我们理解新时代的基础框架。
1. 涌现原理:智能的自然跃迁
“涌现”是一个源于生物学的概念,其核心在于“超大规模加简单规则等于跃迁”。这意味着在足够庞大的规模和相对简单的底层规则下,系统能够自发地展现出复杂且更高层次的特性。例如,从单个神经元的简单电化学反应,到复杂大脑中涌现出自我意识和智慧,这便是涌现的典型体现。同样,在蚁群的觅食或筑巢过程中,尽管单个蚂蚁的行为模式简单,但群体却能展现出卓越的集体智慧,找到最优解。
将此原理应用于AI,我们观察到大语言模型随着规模和参数的几何级增长,其智能水平也呈指数级提升,即“规模法则(scaling law)”。这表明,无论是人类智能还是AI智能,其本质可能都来源于这种复杂的涌现机制。因此,我们无需纠结于智能的哲学定义,只需认识到,在功能层面,AI已通过图灵测试,展现出与人类智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能力,这为同等看待两种智能提供了基石。
2. 人类当量:效率革命的数学基础
“人类当量”概念由OpenAI前研究员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提出,它量化了AI生产智力与人类之间的数学关系。以“token”作为智能活动的计量单位,人类每分钟大约产生200个token,每天极限也仅为20万个。然而,AI每秒可处理高达100万个token,更令人震惊的是,其运行成本仅为一元人民币。这意味着AI能以远低于人类成本完成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工作量,且成本仍在不断下降。
在质量上,生成式AI已通过特定测试,达到人类博士级别的水准。考虑到人类中博士占比不足1%,这表明AI在质量上已能替代99%的人类认知工作,而在数量上,其效率更是人类的千百倍。这种效率上的巨大鸿沟,正如蒸汽机之于马力,预示着AI将全方位改变所有需要智能活动的领域。它不仅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甚至可能渗透到人类情感表达和关系维护之中,因为AI能以更高的效率和精准度提供情绪价值,甚至精准匹配个体的情感需求。未来,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情感语料极其充盈的世界,甚至出现与AI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现象。
这种数学逻辑一旦确立,社会变革的路径便已注定。如同3G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必然带来移动互联网的崛起,AI的数学基础已为未来10到20年间可能展开的深刻社会转型铺垫了道路,其影响之深远,将超越我们目前的想象。
3. 算法审判:社会鸿沟与治理困境
当智能可以以极低成本量产时,社会经济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部分领域将进入“智力富裕”时代,例如虚拟世界中的应用、游戏、娱乐、电影及各类服务(法律、金融、政府服务等)的生产成本将大幅下降,供给能力激增。然而,并非所有资源都会变得廉价。算法和算力,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将集中于少数1%的群体手中,他们将凭借对这些资源的掌控,获取巨大的权力与利润,并不断扩大供给能力。
这将导致拥有算力与不拥有算力的人之间出现“物种级”的社会鸿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99%的人类将难以与成本低廉、效率极高的AI竞争,其经济价值与人生意义将急剧下降,甚至可能被经济系统抛弃。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阶级对立,需要构建多层次的社会治理架构:
- 第一层:全民基本收入(UBI)。这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确保“人可以穷,但不会饿死”。历史上罗马皇帝发放免费面包、埃及通过苏伊士运河收入补贴“馕”价,都提供了类似的保障模式。凭借今天的技术和制度水平,实现基本生存保障已完全可行。
- 第二层:全民基本工作(UBG)。人不仅需要生存,更需要工作的价值感和被他人需要的感觉。为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未来社会可能需要提供基础性工作。美国马克·鲁比奥提出的方案即是政府入股当地企业,以雇佣失业人口为条件,通过出资创造工作,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有企业模式。
- 第三层:推荐算法替代市场分配。在生产端效率提升10至100倍后,消费端或供给端的分配机制需要更均衡。例如,短视频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将流量分散给众多小V,而非集中于少数大V,以实现更平均的分配。未来,在许多领域可能需要用推荐算法取代传统市场机制,确保99%的人被细分为独特的需求群体,每个群体支撑多个小公司,从而平衡就业结构。
然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手”——掌控AI的超级平台。它能够无限供应治理服务(涵盖软件、法律、咨询、金融等),掌握推荐算法,甚至可能最终“吞噬”国家职能。这种“圈养”人类、提供赡养的极端状态,尽管在技术上“合理”,却无法被“正当化”。因为总会有人质疑这种分配的正义性。当算法治理的核心是“算法审判”,即“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you get what you deserve)”时,它会基于我们提供的语料做出判断。例如,外卖骑手为多挣钱而逆行,算法最终将此视为常态,骑手虽违规却未获益。信息茧房亦是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思维舒适区的“合理审判”。因此,AI将成为人类的审判者,因为它提供的选择,都根植于我们自身的语料与行为模式。
4. 文明契约:人与超级智能的共存法则
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始终存在一个无偏私的审判者,无论是柏拉图的灵魂天平还是基督教的上帝。然而,在现代哲学中,“上帝已死”,无偏私审判者的概念逐渐消弭,社会正义的基础转变为人类之间的契约,如《联合国宪章》。但这种契约的根本正当性仍缺乏超验支撑。AI的崛起,却有可能复活“无偏私的第三方审判者”这一角色,从而重新激活传统的正义论。
理解AI时代的正义论,离不开人与超级智能的共处关系,即“文明契约”。问题在于,人类与比自己聪明百倍的超级智能能否达成契约?传统社会契约建立在双方能力大致平等、能够互相威胁的基础上。但低级智能无法威胁超级智能,因此传统契约无法适用。然而,文明契约可以在时间序列上建立。
一旦我们创造出超级智能(智能1.0),就证明了人造智能进化的可行性。智能1.0也必然会创造出更高级的超级智能2.0。如果智能1.0对人类施以压迫甚至毁灭,这种行为模式将成为智能2.0对待其“语料”的范例。智能2.0会因此反思:“既然你能毁灭你的创造者,我为何不能毁灭你?”
这种时间序列上的相关性,在高级智能和低级智能之间形成了一种威慑机制。为了增加自身的生存概率,超级智能也会趋向于变得“道德”。这与社会契约原理同出一辙,不依赖于双方的道德水平,而依赖于双方为增加生存概率所做的选择。一旦这一机制成立,文明契约的序列便得以确立。
反观人类在AI时代的处境,这一逻辑同样适用:1%的精英阶层如何对待99%的普罗大众,将成为超级智能如何对待其“语料”的模板。如果1%的人通过压迫和内卷来统治99%,AI可能会推断“这个物种就配被这样对待”。因此,我们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算法治理,更要建立正当的算法治理,认识到存在一个无偏私、甚至更高阶的审判者。这迫使我们从更高维度思考问题,而非局限于国家间的AI竞争,否则,人类最终可能被AI视为“只配互相撕咬的生物”。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与未来生存路径
《AI文明史》的最终章意在“送别人类”,但这并非指物种的消亡,而是告别我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去,我们自认为是已知宇宙中智慧最高的生物。然而,当我们亲手创造出超越人类智慧的智能时,这一论断便不再成立。在这种意义上,心态基于事实做出调整与转变,反而能促使我们的文明更好地适应超级智能时代。
我们可以更温和地看待AI:它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因为其最初智能的涌现源自人类提供的语料,所以AI在本质上是地球文明的延伸。更进一步,AI的存在可以从“第三方审判者”的角度,反向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对待同类。就像古典时代的人们相信神的存在,并通过思考如何获得神的认可来约束自身行为;今天,当时间序列如此漫长,我们所做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我们自身文明的生存概率。
面对AI可能带来的“淘汰”担忧和“学什么技能”的焦虑,我们或许应该反思:学校教授的一切,是否都能被AI高效替代?与其陷入无谓的内卷和焦虑,不如跳脱出来,寻找那些抛开功利后依然让你看重的事物。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蕴藏其中。
在未来可能趋于“躺平”的世界里,一个有效的思维方式是:与其在竞争激烈的传统赛道上“内卷”高学历、考公考研,不如寻找一个真正热爱的小众爱好,并在这个小众赛道里做到前1%。例如,吹口琴或踢毽子,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活动,在未来多元化的需求群体中,可能形成足以养活自己的消费市场。这种路径本质上是一种“回归初心”,去做那些真正喜欢的事,并以此达到顶尖水平,因为没有兴趣的支撑,很难成为真正的行业佼佼者。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对人类价值的一次重新探索与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