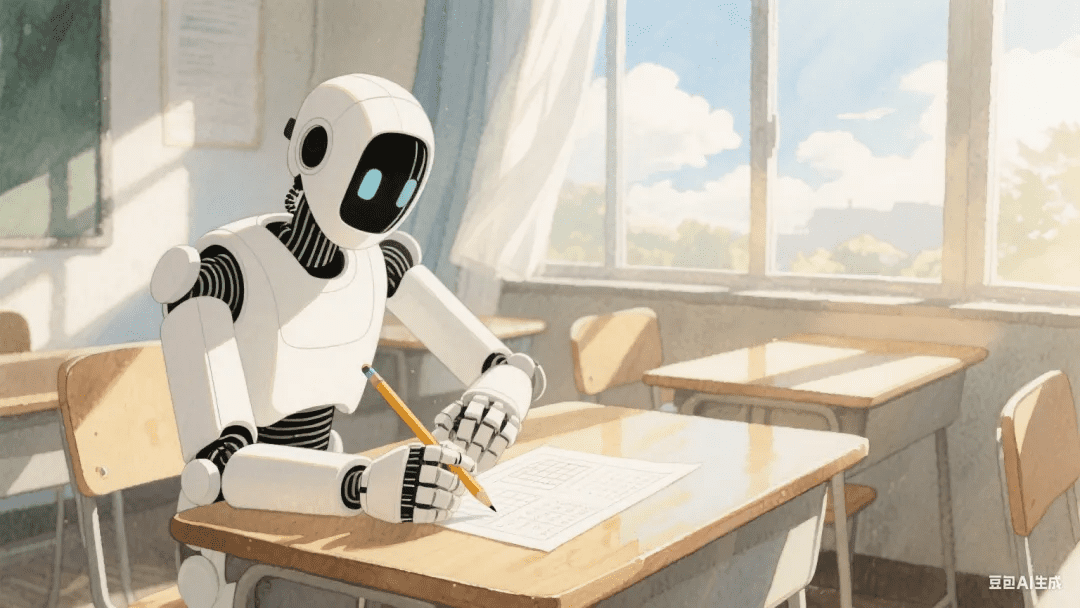AI 高考引发的思考:未来教育与人类价值重塑
高考的帷幕缓缓落下,但另一场“AI 高考”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极客公园近期对多款主流大模型进行了高考水平测试,结果显示,AI 已经具备轻松考入 985 重点大学的实力,甚至有模型版本达到了清华、北大的录取水平。这一消息无疑令人振奋,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类价值和教育意义的重新审视。
7 月 3 日,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与“乱翻书”主理人潘乱、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共同探讨了 AI 在高考中展现出的能力,以及其背后对教育、人类价值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以下是对话的节选,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AI 数学能力突飞猛进:是超越还是另一种学习方式?
张鹏提到,AI 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尤其在数学科目上表现突出,几乎接近满分。这是否意味着 AI 已经具备了顶尖数学家的水平?
张一甲认为,高考数学与顶尖数学研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高考数学侧重于对固定方法和定理的掌握,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可以提高成绩。AI 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将刷题发挥到极致。
然而,真正的前沿数学研究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对复杂概念的深刻理解,以及定义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源于数学家的直觉和科学审美,无法通过题海战术培养。顶尖数学家需要具备创造性,能够在极狭窄的领域内定义问题、概念和工具,推动学科发展。这是目前 AI 与人类数学家之间最根本的差距。
张鹏进一步追问,顶尖的人类数学家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张一甲介绍,以数学竞赛为例,国家级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考察的是学生沉浸式地研究问题的能力,而非高考的快速反应和程式化训练。顶尖的人类选手可以分为两类:科班出身和“野路子”。科班选手接受系统化训练,而“野路子”则更依赖于兴趣、天赋和直觉,能够在没有太多工具辅助的情况下找到解题的突破口。
这种分野可以被解读为两种不同的“涌现”。科班选手是在植入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延展,而“野路子”则更像是一种基于天赋的“人类涌现”,这与大模型基于数据的涌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人类在这两种路径上都能诞生顶尖的人才。
潘乱则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成为真正的数学家,究竟是方法更重要,还是天赋更重要?
张一甲认为,成为数学家的关键要素既不是完全靠勤奋,也不是完全靠天赋,而是动力和自驱力。最关键的是一种沉浸式的、近乎痴迷的兴趣与好奇心。而 AI 目前还缺乏这种内在动力。
推理能力提升:AI 应用迎来新变革
张鹏提到,AI 在理科上的提分主要得益于模型推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推理能力的进步对 AI 行业和应用带来了哪些改变?
潘乱表示,推理能力的提升是全方位的。在生活中,AI 就像一个随身向导,可以随时解答疑问。在工作流上,AI 让他变得更勤奋,例如可以快速整理速记、凝练观点,甚至可以帮助设计提纲。此外,AI 还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例如撰写网络小说。
潘乱还特别提到了飞书的知识问答和谷歌的 NotebookLM,认为这些工具像是给人的大脑加上了外挂和作弊器。
张鹏表示,AI 确实解放了潘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创作中。
张一甲则认为,AI 进入 B 端产业的工作流才刚刚开始。这需要懂行业的人来推动,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还需要理解行业的特定工作流和限定条件。AI 在 B 端的落地更像是“数字化转型的下一阶段”,需要在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慢慢磨合。
多模态融合:降低人机交互门槛
张鹏关注到,AI 在多模态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处理带有图表的题目时表现出色。这说明,要攻克图表题,必须依赖多模态。那么,如何看待大模型在多模态领域的进展?
张一甲认为,多模态最终会成为所有 AI 公司都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多模态交互的本质是降低人与机器打交道的门槛,让 AI 可以直接理解真实的世界,而不需要将所有信息都抽象成文本。无论是图像还是未来的视频,都是在降低人与 AI 交互的门槛。
潘乱表示,多模态的进步已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用 AI “生图”做头像,或者用它来创作歌曲。更典型的应用是“识图”,可以识别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他甚至觉得,离我们打开一个 AI 应用,让它实时阅读周边陌生世界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张鹏表示,大模型最终就是一个模态转换的魔法盒,可以将任何模态的信息扔进去,然后再以你需要的任何模态输出来。
潘乱还提到,各地文旅部门是使用 AI 最勤快的一批人,他们利用 AI 制作各种天马行空的视频,展现各种可能性。
张一甲则表示,自己刷到 AI 生成内容的比例并不高,可能是推荐算法根据个人偏好有所不同。他个人如果看到 AI 内容比例过高,反而会更倾向于看一些真人甚至略显粗糙的内容。早期他对 AI 作图、生成视频很感兴趣,但后来发现,再美的图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 AI 生成的,他就失去了审美和获取愉悦感的动力。
张鹏提到,虽然 AI 考大学已经考得很高了,但它在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事还做不好。对于人类来说,看一张照片和看一段视频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对 AI 就差很多。这反而挺让人兴奋的,因为还有不确定的东西,还有创新的机会。
AI 写作:是助手还是替代者?
张鹏提到,最初人们被 ChatGPT 的语言文字能力所震撼,但今年 AI 在理科上的涨分更多,文科好像反而没怎么涨。这是为什么?
潘乱认为,理科是找规律,文科找自由。大部分理科有标准答案,文科是自由,是艺术,是发散。如果你强调逻辑、数据、推理、效率、标准化,那就像计算器和珠心算一样,它一定更高效、更不出错。理科追求规律和效率,但文科是关于自由的艺术,自由指的是人的情感、价值观、跟社会的互动和表达。
张一甲表示,文科中有些部分是可以的,例如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AI 也能做。但像写作文就不一样了。写作文除了优美、引经据典之外,还需要情感投射、立场、价值观、社会批判性、矛盾张力。这些评价维度都不确定,更何况创作维度。
张鹏问道,作为内容工作者,平时工作中会考虑用 AI 处理一些文字内容吗?有没有观察到 AI 在写作上目前会出现的问题?
潘乱表示,AI 写作最近进步很大。模型在发散、总结、头脑风暴上非常好用。它可以帮你做提纲、拆解、概要,你给它一个模糊方向,它可以连点呈现。这跟推理能力的进步有很大关系。不过,AI 写出来的文章还是容易被看出来是 AI 写的。好的创作者会把它当作一个结构化的助手,一点一点搭起来,最后还需要自己掌握火候。 AI 写作的价值在于它的发散,帮你发散思考。
张一甲表示,AI 更多用于调研、分析、头脑风暴。最后成文这一步他们比较审慎,不完全信任 AI,因为它可能有事实性错误,缺乏反复检查的严谨性。前半程效率提升很大,但成文还是依赖人。
张鹏总结,这是一个“金镶玉”原则:金子是 AI 的能力,把它当作一个框架去支撑内核,内核还是我们自己。最终人还是在中心,AI 是外部的支持体系,不能代替内核。
后 AI 时代的教育:人类该往哪里去?
张鹏提出,AI 的能力快速进步,未来人们的职业发展会有怎么样的变化?现在懂 AI 的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报志愿?
潘乱建议,学个手艺。高薪的中产文理科工作会很快被 AI 侵蚀,这一定是最卷的领域。不如学个 AI 干不好的,例如怎么做金镶玉、雕刻玉器。所有工业化、批量化、方法论化的东西,某一天都绝对会被 AI 超越。
张一甲则认为,大学四年要选最难的专业,例如数学或物理。因为人生很少有四年时间沉浸式地搞一个非常艰难的学问,这对脑力、思维、专注力、意志力都是极强的训练。而且,要从自身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出发,选择专业。
张鹏总结,家长首先要关心孩子想学什么。自驱力是人类最后的阵地。我们对某些东西的热爱,是 AI 不具备的原生特质。同时,要围着兴趣走,早点把 AI 配在孩子身边,用 AI 提升效率,探索、强化学习曲线。
潘乱表示,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现在是一个需要开始关注自我的时代了。因为你再发展你也发展不过 AI。AI 未来是无限的供给,在所有的领域里它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要关心自己,而不是一直关心,我这个社会里面去做哪个牛马和螺丝钉能够有最高的效率,哪的需求供给不够,我就适配哪个。
张鹏认为,更好的策略是首先关注自我。
张鹏继续发问,AI 在考试上已经超过 99.99% 的人类了,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我们多年的寒窗苦读,那应试教育本身,还有意义吗?
张一甲认为,应试教育在高维度智力筛选上是高效的。它筛选出来的尖子生,通常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训练出了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系统性的思维、快速掌握知识的能力,以及专注力、意志力、延迟满足等品质。AI 本质上就是应试教育的终极形式。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强的学生,筛选出的能力,恰好和 AI 的能力其实是正相关的。会应试的人,可能也比较会搞 AI 应试。
潘乱表示,教育的目的绝不应该是继续筛选更多人进入高等学府,而是要培养更多的人,适应未来社会,与 AI 共处。应试教育做筛选很有效率,能快速筛出一批人,但是从社会层面上,它也在让更多的人受害。即使是被筛出来的人,他们也不见得在回望这一生的时候,更幸福。因此,让大家都有基础的知识和素养是更必要的。
张鹏问道, AI 帮孩子写作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应该鼓励吗?
潘乱认为,要分年龄段。大学生当然应该用,但对于心智还未成熟的小学生,过度依赖 AI ,会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你用 AI 轻易就绕开了所有痛苦,那可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成长。
张一甲表示,限制孩子使用 AI 是行不通的。与其围堵,不如接受“AI 无处不在”这个现实,然后去思考,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到底是什么。AI 在孩子成长中的角色会不断演进,从词典,到搜索引擎,再到思维伙伴。真正担心的,是学习的“空心化”——你看起来在学习,也交付了学习成果,但知识和能力完全没有进入你的大脑。这比用不用 AI 本身更可怕。
张鹏总结,今天的教育,对家长的挑战是空前的。必须从关心“结果”,转向关心“过程”。孩子用 AI 交出一份作业,结果可能很完美,但我们要问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你和 AI 共同探索时有什么启发?你有没有定义一个好问题?因为 AI 能轻易地给出结果,所以“过程”就成了人类独有的、真正有价值的教育阵地。
AI 是拉平还是加剧鸿沟?
张鹏提出,现在的 AI 究竟是在拉平还是在加剧教育和信息的鸿沟?对于小镇青年们、孩子们,未来的机会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潘乱认为,主观能动性更强的那些人,机会是变得更大,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会被这个数字鸿沟拉到非常后面去。用好 AI 需要很多前提:你要会提问、能抵抗娱乐内容的诱惑、有付费能力和好的网络环境。AI 理论上是拉平鸿沟的工具,但现实中,它会放大已有的不平等。
张一甲认为,在义务教育和基础医疗这样的普惠层面,AI 会极大地促进公平。但再往上,社会可能会形成新的分配形态。未来,可能会有少数人掌握着具备巨大杠杆效应的“高阶 AI ”,从而分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别人只能做数据提供者和应用者。
张一甲还提到,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要建立一个人的适应能力。AI 极大程度上增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个体要拥有更高的适应性,才能生存。
潘乱总结,你的靠谱、你的认真、你的勇气、你的胆识,人的自我迭代,自学能力,这些是永远重要的。
张鹏问道,从自己出发,当这个技术出现之后,最终我的位置是什么?你们担心自己被替代吗?
潘乱表示,自己一丁点没有被替代的恐惧。因为 AI 发展到现在,社会的资源在当下它并没有变得更多,也没有一个新的平台冒出来。只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大家创作内容的效率发生了变化。在已经有一定连接关系,已经占优的人,其实是处于一个更好的升位的。另外,AI 的核心能力在于“输入”,也就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人的“输入”能力是不均等的,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夯实我的输入能力。
张一甲表示,我们都需要在开放环境定义一个封闭的问题,并为之承担风险。这个过程需要的是信念和坚持,是 AI 无法替代的。另外,我对人本身有信心。生命是熵减的,有自由蓬勃的力量。即便 AI 在各项技能上都超越人类,但人作为生命体,一定会发挥其独特的生命力,去寻找到“生而为人”的意义感。我永远站在人类这边。
张鹏表示,自己特别希望被替代。希望 AI 能够替代某些我已经熟悉的事情,让我能被解放出来,去探索更多未知的新领域,让我们的一生能活出几辈子的精彩。人类最宝贵的是无知无畏的力量。所有伟大的创造,都源于此。AI 应该支持我们的无知无畏,它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能降低我们探索的代价。所以,我希望 AI 能够大步快跑,帮我们捍卫自己内心的那股力量,那才是生命最本质的、熵减的状态。